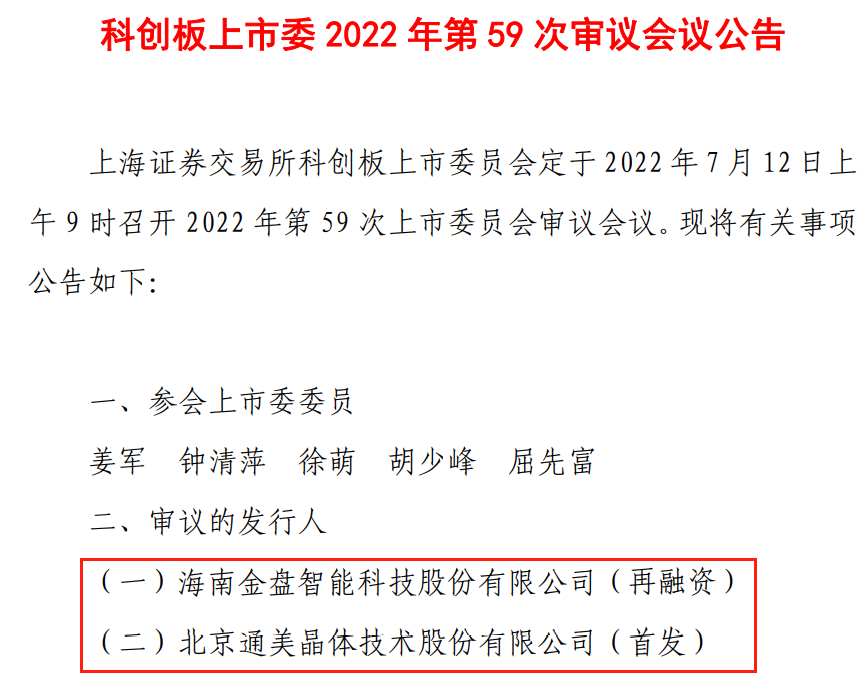■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佛像(局部)作者/供图
那时人们见到的地面文物,已经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直到元代末年,仍然有人熟悉西夏的语言文字,而且能用西夏字写作短小的文章。对此最著名的证据就是北京居庸关云台券洞内的“六体石刻”,那上面有一篇用西夏文写的《造塔功德记》,时间在元至正五年(1345),这时距离西夏覆亡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有余。进一步的回答出现在半个世纪前——人们又得到了两个明确的证据,即今存故宫博物院的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刻本,以及今存河北保定莲池公园的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这两件文物上面都有明代的时间题署,分别为宣德五年(1430)和弘治十五年(1502)。《明会典》卷141有“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其中说:“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这条规定颁布于保定经幢建立后不到十年,目的是强制包括党项人在内的色目人与汉人通婚。可想而知,禁止少数民族在族内通婚的法令一旦在中原实行,将很快使党项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由此不妨把1502年视为西夏文字应用的时间下限。这就是说,直到明代还有党项人能够熟练地使用西夏文。
 【资料图】
【资料图】
然而,短篇题记的发现只能证明当时还有个别人保持着对西夏语言文字的记忆,并不能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当初西夏皇室曾组织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导致出土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佛教著作的西夏文译本,同一种佛经甚至会被反复抄写多次。这使人相信西夏人对佛教的热情几乎可与西藏比肩,西夏时代的党项人对佛经也有极大的需求。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西夏覆亡之后,还有人用西夏文来翻译刊印整部的佛教著作吗?或者说,西夏文的佛经还在党项人中间传播吗?
此前已经知道,在西夏覆亡之后,有一些党项族的僧人从贺兰山进入内地,辗转南下杭州,自称“白云宗”教徒。从1270年开始,他们两代人花费了40年的工夫编集刊印了两套大藏经,即汉文的“普宁藏”和西夏文的“河西藏”,中国佛教文献史也由此进入了“后西夏时期”。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一部宁夏灵武出土的元刊西夏译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尾有一篇皇庆元年(1312)的发愿文,其中详细记述了“河西藏”的编刊过程,表明编集刊印“河西藏”得到了元代朝廷的支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到整理西夏文佛经的具体工作是“校有译无”,即校订已有的译本,并且补充翻译此前没有翻译的著作和丢失了译本的著作。这样看来,元代僧人曾经用西夏文新译过整篇的佛教作品,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如此,由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里没有出现元代的年号,所以国内外一直有个别学者轻率地认为元代没有西夏文作品产生,这种看法在佛教史学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会。
很明显,要消除这个误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汗牛充栋的西夏文佛经中发现元代翻译的整篇作品,从而为“校有译无”提供实际的样本。为此值得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正在进行的一个科研课题——“基于中国民族古文字冷门绝学人才传承培养的民族文献语言学学科建设”,这个课题的任务之一正是寻找和鉴定“后西夏时期”的西夏文佛教著作译本。
■私人藏《喜金刚现证如意宝》的首尾题作者/供图课题组找到的最确切证据来自日本天理大学收藏的一件佛经刻本。西田龙雄(1928—2012)在20世纪中叶研究过这本小书,正确地鉴定出其主体部分是译自藏文的《无量寿宗要经》,但是忽略了经文后面所附的《出有坏无量寿智莲华鬘章赞叹》和译刊题记。《莲华鬘章赞叹》由开头的小序和52句偈颂组成,下面是小序的汉译:
《出有坏无量寿智莲华鬘章赞叹》。此者,如实宣说佛言正理,八思巴帝师所集,戊午年娄宿月初八日合毕。卷尾的翻译题记汉译如下:
发愿译者甘州禅定寺内比丘斡玉德妙法师。 禅定寺法堂讹正德法师室内译。 癸巳年神足月十五日,译主党宝幢吉贤番译。 从小序和题记可以知道,这篇作品是元代首任帝师八思巴(1235—1280)在戊午年(1258)创作的,并于当年的藏历九月八日附在了《无量寿宗要经》的后面。在八思巴去世后的癸巳年(1293),由一名出自张掖的僧人发起组织了一个翻译小组将其译为西夏文。小组成员的姓氏“斡玉”“讹”“党”表明他们都是党项人,首席译者采用了“宝幢吉贤”作为法名以宣示自己的藏传教派,这个名字还原成藏语是“贡却坚赞班藏卜”(Dkon mchog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只不过人们迄今还没有能够在藏文史料里找到他的生平信息。课题组进一步指出,八思巴帝师的这个《莲华鬘章赞叹》最初是一篇独立的作品,藏文原题Bcom ldan ’das tshe dang ye shes dpag tu med pa la bstod pa’i tshig padmo’i phreng ba zhes bya ba ’di ni,连同小序一起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里,日本收藏的这个本子是与《无量寿宗要经》合并刊印的。
课题组注意到的另一个关键证据于2015年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原件为来历不明的私人藏品。这是一个保存基本完整的手写长卷,卷首题“喜金刚现证如意宝上卷”,卷尾题“喜金刚现证定次上卷”,下面附有音译的藏语“阿帝”二字,然后是左面的一行翻译题记——“衣衲慧增与藏文重校详定”。这件经文也是译自八思巴传授的藏文本,藏文原题dpal kye rdo rje’i mngon rtogs yid bzhin nor bu zhes bya ba ’di,全文同样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里,而且在卷尾还另有一则藏文题记提供了关键的信息:
dpal kye rdo rje’i mngon par rtogs pa yid bzhin gyi nor bu zhes bya ba ’di / sa pho rta’i lo dbyu gu’i zla ba la / rgyal po go pe la’i pho brang chen por sbyar ba’o //可以翻译如下:
此《喜金刚现证如意宝》系八思巴于阳土马年藏历九月作于汗王忽必烈之大殿。藏历“阳土马年”相当于1258年,也就是八思巴完成《莲华鬘章赞叹》的同一年。即使西夏译本并未记录翻译的时间,似也不妨估计它完成于1293年前后。如果有人因为是私人收藏而怀疑这个写卷的性质,那肯定是与学术研究无关的妄议。
以上两种作品都译自藏文,都出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这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西夏特藏——既然那座塔里存有大量元代的绢画,似乎就应该也存有同时代的西夏文书籍,只不过上面没有明确的时间题署,人们一直没能将其辨认出来。
俄罗斯的西夏学家克平(Ксения Б. Кепинг,1937—2002)在多年前曾首先尝试对此给出肯定的回答。她注意到的是一本手抄的西夏文诗集,其中有一首诗描写的是战争带来的恐怖景象,里面出现了一个很罕见的词。她把那个词解作“铁匠”,认为是成吉思汗名字“铁木真”的意译,于是判断全诗是西夏覆亡之后党项人对蒙古征伐的回溯。平心而论,她对那个西夏词的考证有些牵强,所以没能得到西夏学界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进一步做出的鉴定值得重视。课题组首先注意到的是俄国收藏的一个完整的刻本,书题译作“正行集”,写作目的是假借佛教之名向信众传布中原式的道德说教。这部书据以翻译的汉文原本最初被收入“普宁藏”,通行本载于《中华大藏经》第71册,作者是佛教白云宗的始祖清觉(1043—1121)。清觉俗姓孔,于宋元祐八年(1093)在杭州自立宗派,不过当时并未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元代那批南下杭州的党项僧侣拾起了白云宗的衣钵,并在元朝廷的支持下成了当地佛教事务的总管,很快使这个宗派的势力盛极一时。经皇帝批准,他们得以把其祖师清觉的《正行集》刊入普宁藏,使得这本并非出自印度大德且不受世人重视的著作得以流传。由此想来,俄国所藏《正行集》的西夏译本极有可能产生于编刊“普宁藏”的杭州,尽管这个刻本上面没有写明翻译的时间。
类似的还有俄国收藏的《三代相照文集》刻本,这是自清觉以下白云宗三代祖师的诗文汇编。书的卷末有一篇发愿文,落款的人叫“慧照”,应该就是发起雕刊普宁藏的“白云宗主慧照大师”,时间自然是在雕刊“普宁藏”的13世纪80年代前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发愿文在最后祝愿“当今皇帝谨持佛位”,“当今皇帝”是元刊“河西藏”卷首祝愿的典型用语,与西夏时代发愿文仅称“皇帝”至多加上尊号的习惯不同。因此说,尽管至今没有见到相应的汉文原本,但可以想定这本书是元代党项僧人搜集汇编其祖师的作品之后译成西夏文的。
沿着《三代相照文集》的线索可以鉴定俄国收藏的另一件写本《三观九门枢钥》。该书的内容是阐释唐代宗密所述“圆觉三观”的义理,后面附有白云释子所作的一首《道宫歌偈》和一首《了悟歌》。索罗宁(Кирилл Ю. Солонин)最近指出,这两件作品与《三代相照文集》卷首所收的《白云释子道宫偈》和《白云大师了悟歌》内容相同,只是因出自不同的译者之手而导致译文用词有些差异。课题组由此判定,《三观九门枢钥》也应该是元代的译作。尽管至今同样没有见到相应的汉文原本,但“白云释子”和“白云大师”指的都是白云宗始祖清觉,这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可以估计为元代翻译的作品还不止这些,但课题组提出的以上五种译著已经足以证明西夏语文在元代仍有旺盛的活力。这五种著作或译自藏文,或译自汉文,大概都是13世纪末编刊“河西藏”期间的作品,其中有三种以刻本形式流传,更进一步证明西夏文书籍在当时仍有固定的读者群体。
作为历史的常识,一个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字大都不会随着政权的灭亡而立即遭到弃用。众所周知,辽王朝创制的契丹字一直沿用到金代中期,金王朝创制的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代初期,而清王朝创制的“清字”在今天仍然被新疆的锡伯族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由此想来,西夏字并未随着西夏王国的覆灭而被马上废弃,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只不过这种文字在那以后还应用了将近三百年,其时间比人们预想的要长,而且在元朝佛教“后西夏时期”的活力也是此前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这里面的原因也许应归于元朝的文化包容态度。在大一统的帝国正式建立之后,元朝统治者对治下的各民族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这在保证国内局面稳定的同时宣示了对不同民族的尊重,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有了汉、蒙古、回鹘、西夏等文字的文献在元代的大量产出,以此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储备和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关键词: